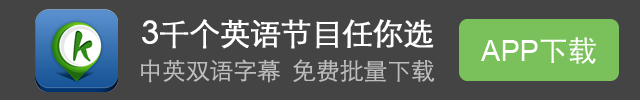(单词翻译:单击)
名著阅读
The prodigal son was evidently nervous of visiting the parental abode; but Mr Carker pushing him on before, he had nothing for it but to open the right door, and suffer himself to be walked into the midst of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mustered in overwhelming force round the family tea-table. At sight of the prodigal in the grasp of a stranger, these tender relations united in a general howl, which smote upon the prodigal's breast so sharply when he saw his mother stand up among them, pale and trembling, with the baby in her arms, that he lent his own voice to the chorus.
Nothing doubting now that the stranger, if not Mr Ketch' in person, was one of that company, the whole of the young family wailed the louder, while its more infantine members, unable to control the transports of emotion appertaining to their time of life, threw themselves on their backs like young birds when terrified by a hawk, and kicked violently. At length, poor Polly making herself audible, said, with quivering lips, 'Oh Rob, my poor boy, what have you done at last!'
'Nothing, mother,' cried Rob, in a piteous voice, 'ask the gentleman!'
'Don't be alarmed,' said Mr Carker, 'I want to do him good.'
At this announcement, Polly, who had not cried yet, began to do so. The elder Toodles, who appeared to have been meditating a rescue, unclenched their fists. The younger Toodles clustered round their mother's gown, and peeped from under their own chubby arms at their desperado brother and his unknown friend. Everybody blessed the gentleman with the beautiful teeth, who wanted to do good.
'This fellow,' said Mr Carker to Polly, giving him a gentle shake, 'is your son, eh, Ma'am?'
'Yes, Sir,' sobbed Polly, with a curtsey; 'yes, Sir.'
'A bad son, I am afraid?' said Mr Carker.
'Never a bad son to me, Sir,' returned Polly.
'To whom then?' demanded Mr Carker.
这位浪子显然害怕走进父母的住宅;但是卡克先生推着他向前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开了他自己家里的门,听任自己被领到簇拥在家庭茶桌周围的许多弟弟妹妹中间。这些年幼的亲人们看到浪子被抓在一位陌生人的手中时,都一齐嚎啕大哭起来;当浪子看见母亲手中抱着婴儿站在他们中间,脸色苍白,身子颤抖的时候,哭声锋利地戳痛了他的心,他自己的声音也加入到这个异口同声的大哭中了。
毫无疑问,这位陌生人不是凯齐先生本人,就是他同伙中的一位;全家年轻人更加高声地嚎啕大哭起来,而那些比较幼小的就像那些被老鹰惊吓了的小鸟一样,背倒在地上,猛烈地踢着脚。终于,波利提高了嗓门,嘴唇颤抖着说道:“啊,罗布,我可怜的孩子,你到底干了什么事啦?”
“没干什么事,妈妈,”罗布用凄惨的声音哭着说道,“你问一下这位先生吧!”
“别惊慌,”卡克先生说道,“我是想为他做好事的。”
听到这个声明以后,一直还没有哭的波利开始哭起来。年龄比较大的图德尔们原先想来营救的,这时放松了紧握的拳头。年龄比较小的图德尔们簇拥在母亲的长外衣周围,从他们胖鼓鼓的小手下面偷看着他们的走上邪路的哥哥和他的不知名的朋友。每个人都为这位有漂亮的牙齿、想做好事的先生祝福。
“这小子,”卡克先生把罗布的身子轻轻地摇了一下,“是您的儿子,是吧,夫人?”
“是的,先生,”波利行了个屈膝礼,抽抽嗒嗒地说道,“是的,先生。”
“恐怕是个坏儿子吧?”卡克先生说道。
“对我来说,他从来不是个坏儿子,先生,”波利回答道。
“那么对于谁他才是呢?”卡克先生问道。
背景阅读

本书简介:
《董贝父子》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发表于1848年。小说描写了董贝父子公司的盛衰史。董贝是个贪得无厌的大资本家,妻子儿女都成了他追逐利润的工具和摆设。公司经理卡克尔是个奸诈小人,骗取了董贝的信任后又一手造成了他的破产。在现实的教训中,董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最后,虽然他已无法重整家业,却成全了真正的家庭幸福。
书评: 董贝怎么可能幸福?
来自: 暂停(豆瓣网)
董贝是《董贝父子》的主人公,这个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是风光一时的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据说是“19世纪企业精神”的象征。
说到企业,先得比规模,在董贝眼中,“世界是为了董贝父子经商而创造的,太阳和月亮是为了给他们光亮而创造的。河川和海洋是为了让他们航船而构成的;虹霓使他们有逢到好天气的希望;风的顺逆影响他们实业的成败……”,他的公司称霸四海,以至于董贝自认是世界的中心。看这气势,怎么着也不比“真功夫”之类的中国家族企业小。而这个1840年代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之先的企业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为他的家族企业寻找继承人。为了生个堪当大任的儿子,董贝精心购买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而这正是他事业与人生崩溃的开始。
网络、风投,这些今天中国富豪们嘴里的名词,董贝听都没听过的。但人们为之困扰的问题,其实最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状况。从家族企业内部对财富继承与财富分配的纠结与冲突来看,2010年代的中国商人仍然在为董贝在170年前所痛苦的事情寻求解决。解决得不好,夫妻反目或者兄弟阋墙的例子不在少数。而整本《董贝父子》,与其说在讲述富翁的商海风云,不如说在告诉我们,把商业逻辑引入家庭所导致的不幸。
如恩格斯所说,董贝是一个“除了快快发财以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快乐”的人,当他的贸易帝国土崩瓦解、失去了唯一的快乐来源之后,董贝企图举刀自杀。女儿却用爱感化了他,他最终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需要得到宽恕”,随之步入幸福的晚年。
乍听起来,今天的中国富商或许该羡慕英国前辈重获幸福的运气,但必须负责任地追问一句,董贝的幸福如何可能?原本已经与资本“人剑合一”的董贝,怎么可能好象换了一个人一样?
这个提问并不苛刻,早就有人认为,董贝的转变毁了一本出色的小说,董贝的幸福是浅薄无力的,因为他根本没有解决家族企业面临的核心矛盾。换个角度说,他们不相信董贝在失去公司、失去财富之后还有可能幸福,他们也不相信那种唤醒董贝的爱,他们认为让爱出场显得很蹩脚,还不如设计成——董贝中了彩票,解决了债务危机,公司于是免于破产,他又娶了一房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娇妻——更有说服力。
决定人们想象力边界的是他的价值观。董贝在最窘迫的时候,看到了人生的真相。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被带到一个环境里,显出我们最深刻的内心需要,显出我们的本来面目,让我们无可推委,“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这恰恰是改变的机会。我们不求离开世界,只求不被世界的冰冷所制。当然,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或者任凭败坏的部分在我们生命里扩散,或者像董贝一样,承认自己的过犯,把生命的锚挂在他原先生存的平面之外的点上,因着这种联合,他得以更新生命,幸福因此成为可能。
而对于依然俯身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来说,平面之外的任何事物,几乎都是不可理解的。这个世界不是明明服在金钱支配之下吗?服在物质的规律之下吗?服在市场的法则之下吗?无论小学大学,还是EMBA总裁班,都在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这些,恨不得用混凝土把我们的心砌成一座空坟,生怕我们对于灵魂产生一丁点想象力。几乎所有与幸福有关的细节,都被不约而同地省略了。最终,一个人拥有了不受环境不受金钱影响的幸福的可能,竟然彻底成为一件不可理解之事,好象他不可思议、无可救药地堕落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大的神迹是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到历史里寻找另外一个“不可能”的故事,来帮助我们理解董贝的可能。
与董贝同时代的沙夫茨伯里伯爵,通过六十年的努力,推动国会先后通过煤矿法令——禁止妇女和女孩在井下工作、精神病法令——确保精神病人获得人道对待、十小时工厂法令——管制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公共宿舍法令——改善穷苦阶层的住宿条件,他还创立收容所、救济院、“贫民免费学校联盟”,被公认为改变了整个英国的社会状况。
1885年他去世的时候,万人空巷,人们举着布条,上面写着“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是《圣经•马太福音》里耶稣对门徒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是关于爱的教训,无数英国人受益于沙夫茨伯里伯爵对爱的信心,尽管这爱、这信心,无法用理性证明,无法用股权分割,无法委托交易转让。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将近一百年里,发生在英国的宗教大复兴,裨补了工业革命的弊端,大大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带来废除奴隶制度、监狱改革、抑制赌博和决斗的改变,使英国不至在积累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因为尖锐的阶级对立而掀起类似法国大革命的血腥灾难。这为大时代里的个人幸福,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可能性,董贝的重获幸福正在这种可能性之下。
当董贝沉浸在资产负债表里,浑然不知自己可能拥有另外一种活法。所幸当他主动或被迫从自己的营营役役里抬起头时,被这样的时代氛围所提醒,逃出了资本理性、经济原理对心灵的辖制。
幸福并不需要对金钱弃之如粪土,在家庭关系里也不必耻于言利,人类正常健康的感情并非如此脆弱敏感。只是我们的环境里实在缺少一个合适的声音,既遥远又近切,值得我们信赖的声音,远得仿佛来自永恒,近得仿佛体贴入微,在遭遇纷争、血气乍涌的时候轻声提醒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