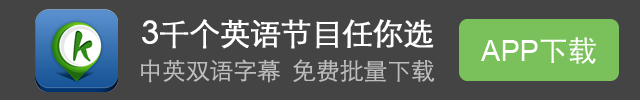(单词翻译:单击)
[导读]在牛津的那些日子不仅让我改变了很多,更多的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牛津的学风深深的影响了我,也希望在这的介绍能影响你们每一个人,同时也为留学新人铺路。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三个不同的境界。我所经历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多着力于解惑,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提问,老师回答。在一问一答的反复中,力求达到授业的目的。然而传道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追求,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诸多先师的轶事中向往一下子而已。一直到读研究生(论坛) ,才有机会跟老师所谓耳濡目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授业和传道,学习做人的道理。我大学毕业以后到英国读书,之后辗转美国,待过一些名校,逐渐积累了一些茶余的谈资,三五朋友闲聊,偶尔也拿出来说道说道。
在牛津的时候,我的导师老K是一个传统的威尔士人,矿工的儿子,家族里第一个博士,第一个物理学教授。初次见他是在酒吧,他喝得有点高,趴在耳边跟我说:有事情找我,我是你老板。做物理的,碰到困难是家常便饭,百思不得其解,常常发信给他,说我愁啊。他发信过来说:到我办公室来开心一下。于是我跑去,跟他闲聊一阵,听他讲笑话。出来的时候会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好的老板能给学生快乐,这算个例子。老K那个时候开始学中文,每周五下午,他给我讲一个小时物理,我给他讲半个小时中文,然后一起去酒吧。老K总请我喝一杯比利时啤酒,我会买几包猪皮干,全组的人都在,大家东拉西扯,聊个痛快。老K平时很忙,见面要跟秘书预约,但周五的酒吧聚会,他是不会缺席的,这也成为我们交流聊天最多的时候。
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师生恋,我说这个在中国挺能被接受的。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中国学术圈里往往把它传为一段佳话。文人辈出的北大,尤其是这样。老K的评论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在大学里这样的事情是要避免的,因为爱情这件事情两个人在心理层面上应该是对等的,而师生关系有太多不平等在里面,作为老师的一方,完全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让学生就范。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老K自己身上,即便是流言蜚语,他都要辞职的,至少学术圈子是不用混了。这个大概算是文化差异,师生恋发生在英国,一定是丑闻而非佳话。
我到美国做了一年多博士后,不是很顺利,看到做物理的一个个都跳上华尔街,自己也想试试。开会的时候见到老K,除了讲述这一年多的辛苦,我问他,如果我放弃物理,去华尔街,他会不会失望。他回答说,他的每个学生开心,他就会开心,不管做什么选择,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守,夫子循循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我那时希望能像先生那样感染一些年轻人。
学术圈子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这个在国内国外哪儿都一样。师生之间也有不公平的对待,有跟导师关系好而一帆风顺的,也有关系不好而处处碰壁的。我有个印度师弟,系里另外一位老板的学生。做研究生有时会有一种非常糟糕的情况,就是老板认为你能力有问题应该听从他的建议,然而学生偏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没问题。结果在错的方向上越走越远,而老板认为这个学生完全听不进去建议,能力实在不行。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欢而散,学生自己断送了前程。我这个师弟大概如此,他从没有跟我详细说过他跟导师间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只是读博士读到最后一年,他导师要他转成硕士毕业走人。印度师弟为人善良,平时大家相处不错,作为师兄我也不知如何帮他,于是我去问老K。老K那时已经是理学院的院长,很有些办法。听完师弟的遭遇,老K说:“这个事情交给我了,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修改制度。”
师弟最后还是没有能留下来,这也许是牛津的游戏规则,一个老板作出的决定,另外一个老板即使权力再大,也没法干涉。然而在老K的指导下,师弟利用在牛津的最后半年,完成了两篇论文,又由老K推荐到加拿大一间学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三年后也顺利博士毕业。而老K给他指点的那个方向,在这师弟的手里也发扬光大,成了独树一帜的课题。
我住的学院第一年有宿舍给研究生,第二年要抓阄,第三年基本不可能住在学院里,需要自己找房子住。在享受了两年学院宿舍的方便之后,我要开始自己想办法了。一天路过门房,看到一则招房客的广告,房东是学院里一位老先生。于是我就去看房,老先生告诉我他是mythologist,我第一反应是哈利波特,难道牛津还真有这门学问?后来才明白老先生是研究古印度和西藏神话的,他说他那书房里好几架子的西藏神话书,随便我看。住了几个月,有天早上吃早饭,老先生跟我说,有件事情要请我帮忙。他们夫妇俩要去西班牙跟女儿过圣诞节,离开三个星期,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两只猫,要我帮忙早晚各喂一次,作为回报,这个月的房租就免了。举手之劳我倒有点受宠若惊了,圣诞节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他们从西班牙寄来的卡片和巧克力。
牛津第N次拒绝给撒切尔授荣誉博士
我在牛津的时候碰到了一次选举。老校长去世,要由牛津校友和在校生选举产生新校长。有人说克林顿吧,有人说彭定康。选举那天,大家排着队进入沈东尼亚剧院,每人发小纸一张。我的那张上面写着,某某爵士(Sir),某某女爵(Lady),我既不认识也没听说过,但Mr.ChrisPatten(彭定康先生)我是知道的。投票者按照个人喜好排名上交,虽然我把彭定康排在最后,但结果揭晓了他还是当选。我一直以为牛津的校长是女王或是政府任命的,这个选举,算是开了眼界。
前几天听说撒切尔夫人又去牛津要荣誉博士的头衔了,这次牛津以738票反对,319票赞成一如既往地否决了给老夫人戴荣誉博士的帽子。虽然谁都清楚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给牛津带来怎样有形的无形的利益。但20多年来,学者们因为铁娘子在任的政策给学术界带来的损失绝不放过她。老夫人这点心愿看来是难了。
在伯克利的时候我赶上了加州政府要倒闭。为了渡过难关,州政府对大学经费削减百分之八,州立大学涨学费30%。这无疑激怒了学生,有学生占据教学楼,阻碍上课,有学生游行支援。警察维护治安,用警棍驱散人群。有老师挺身保护学生,被警察按倒在地,铐上手铐。推上警车的时候,老先生大喊,我是生物系的教授,这是伯克利,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那一刻,让我看到了伯克利这个学校的灵魂,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历史。
在牛津物理系发论文老板排名在最后
1995年物理学界有件大事,美国三个小组几乎在同时得到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爱因斯坦75年前预言而实验上寻找了几十年的东西。谁都清楚,这是个一定拿诺贝尔奖的工作。其中之一的Randy小组,为了证明他是第一个做成功的,在实验结果上先后作出两次不同的解释,这个做法在学术圈里被认为非常的不专业。这件事情的后果,不仅让他失去了6年以后的诺贝尔奖,而且波及到他在学术圈的声誉。十几年来,虽然Randy兢兢业业的做科研,但每每有新的成果发表,常受到同行的质疑。有一年美国原子分子物理年会,要奖励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Randy的,我那时在场,就觉得Randy的学生这次肯定要吃亏。果不其然,优秀论文奖由两个学生分享,Randy的学生偏偏没拿到。我跟Randy有几面之缘,面试过他的博士后,申请绿卡的时候请他写过推荐信,后来开会的时候也一起吃过饭。Randy人到中年,十几年前的锋芒毕露已看不出来痕迹。谈起那次失误,他倒是看得开了,但告诫学生们,这是个教训,不要用科学的严谨性来挑战学术的良心。
想起另外一桩事情,那时候我们一些人写一篇投给《自然》杂志的文章,大家一起在德国开会,老K因为工作繁忙,只派了博士后和我去。文章写完,自然要把老板的名字挂上,拿给老K看。老K看罢说他没有参与太多的实验和讨论,还是不要写他的名字好。但也有不同的例子,在伯克利那会儿,隔壁教授缪勒以前是朱棣文的学生,近两年发表的文章里有位合作者跟我相识。我便问起这位作者的近况。缪勒竟然说他两年前就离开了,到哪里他也不知道,但因为以前这位老兄在实验上花了很多功夫,所以最近这次实验上发的文章,一直还有他的名字。
牛津物理系有个排名的习惯,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最前,辅助者其次,博士后再其次,老板最后。我一直以为这是定则,但这些年听说国内因为导师占据学生的研究成果而署名在前,多多少少让我吃惊了。对待名誉和排名多少从容些,不失是个做老板的样子。
出国那会儿,我是个改良派,现在算是个保守派。对国内的情况,我们这些新海归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东方有东方的风俗,西方有西方的文化。空投回来指指点点的,难免会对不住打拼着的同胞,所以只去讲些故事,既没有批评谁的作风,也没有改变现状的宏图志愿。事情慢慢来做,要想好起来,颇要有点铺路工人的韧性,不矫情,不懈怠,万里之行,由此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