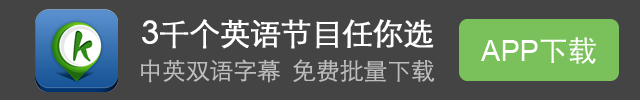北外翻译笔记讲义:翻译与文体 诗歌翻译(2)
日期:2013-02-21 13:52
(单词翻译:单击)
(二) 诗歌的翻译
如果说翻译难的话,那么最难莫过于译诗了,尤其是格律诗,所以古今中外常有"诗不可译"的声音。其实,说"诗不可译",主要是指诗味难译,诗的音韵美难译,并不是说诗歌不能翻译。再者,诗有不同的诗:有的明白畅晓,有的艰深晦涩,有的韵律严整,有的不受律法所限。译诗者也有水平高低之分、技艺优劣之别,所以更客观地讲,诗难译但并非不可译。
一般说来,语言形式服务于内容,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就诗歌而言,形式的意义远远大于散文类作品中的语言形式。诗之所以成为诗,怎样说与说了什么同样重要,所以译文中追求形似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我国的译诗史上,有将英语格律诗译成元曲形式的,有将它译成五言古体形式的,还有用骚体译出的。但目前看来,采用这些形式都值得商榷,因为英语诗人绝不会写出唐诗宋词。同样的原因,把英语格律诗译成散文或散文诗(如梁遇春译雪莱的A Lament)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诗歌的形式是有意义的。英文格律诗汉译的另一种方法是"以顿代步",即以汉语的"顿"代替英语的"音步"以再现原诗的节奏。"以顿代步法"通常强调原文的韵式也应在译文中加以复制,即如果原文的韵式是ABAB、CDCD,那么译文也应有同样的韵式。所谓"顿",是指两个、三个抑或是四个汉字放在一起,它们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同时又形成语音的一种自然的起落。这确实有点像由轻重抑扬构成的音步。以这种方法译诗,是译者追求形似并再现音美的大胆探索,而且确实也产生了一些形神皆似的译作。不过,在顿与音步的对等方面以及顿在何处(即在何处停顿)等问题上,翻译界仍有争议,译者自己有时也难以把握。英语格律诗的另一种译法就是放弃韵律,用自由体翻译,持此论者的理由是原诗节律在汉语中无对等物,译诗重在传达神韵,形似难求且束缚表达,因此不如弃之。在追求形似上,我们认为,王佐良先生提倡的"以诗译诗"是完全正确的,诗歌毕竟不是散文,因此,原诗如果有韵,那么译诗也应尽量沿用;原诗如果无韵,译诗也应无韵,即使用韵,也不能太过整齐,只应是个别诗句中用韵。原诗的节奏应尽量用汉语的自然起落体现,但不可偏执,非要找到所谓"顿"与"音步"的等量齐观不可。形似应尽量在用韵与否以及诗行长短上予以体现,这样既保存了原诗的形,又再现了原诗的音美。当然,诗之最大功用是言志言情。传达情志当为译者首先必须考虑的事情。对于大多数诗来说,形式虽也有意义,但相对于诗之神韵和意境而言,它仍处于次要地位。英汉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常要求译者"变换说法",即变换形式以求神似。比如我们虽不赞成将英语格律诗全都译为中国五言或七言诗,但以这种形式译出的某些诗如能做到传神,却也不失为好的译作。诗歌形式中确有一些不可译因素,但诗的意义、意境、神韵却大都可以被意会、被言传,尽管难以全部传达。因此译者应在词语的锤炼上下苦功夫,写诗者常常是"语不惊人誓不休",译诗者没有这种精神也休想"译语惊人".试比较下面一个英语诗节的汉译: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牛羊相呼,迂回草径
农人荷锄归,蹒跚而行
把全盘世界剩给我与黄昏 (郭沫若译)
译文二:
晚钟响起来一阵阵给白昼报丧,
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声起落。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
把整个世界给了黄昏与我。(卞之琳译)
译文三:
晚钟殷殷响,夕阳已西沉,
群牛呼叫归,迂回走草径,
农人荷锄犁,倦倦回家门,
惟我立旷野,独自对黄昏。(丰华瞻译)
二、 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翻译
(一) 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语言特点
剧本与小说、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对话写成的。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小说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读(当然也可以朗读),而剧本却是最终要诉诸声形的(当然也可以拿来默读)。剧本中的对话(对白)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经过作家精炼后的诗句,如莎士比亚的诗剧中,人物语言多是诗的语言,正式程度较高,辞格也较多。第二种是经过作家加工后的较为正规的、完整的语言,它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再一种就是未经加工的生活语言照录,多停顿,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语法规范句,多重复。当然,上述三种只是大致分类,在每一种类型中,语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语特点又会因人物的年龄、性别、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话语单调乏味,有的人则出语机智幽默,有的人言语矫柔造作,有的人则语言朴实自然……总之,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语言。
(二) 剧本的翻译
翻译舞台剧剧本和影视脚本,要充分考虑其上述特点,译好人物语言,充分体现原剧整体语言特色和具体的每个人的语言特色,使语言连同人物一起"活"起来,"动"起来。就舞台剧剧本的翻译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该剧在另一个国度用另一种语言演出服务,二是译出来供人阅读。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译者都应考虑原文作为剧本的特点。如朱生豪在译莎士比亚剧本时,常常要让自己扮作剧中人物,拿译出的句子读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如果戏剧翻译是为上述第一种目的,译者应尽量使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传达原文剧中人物的意趣,遇到习语典故,应尽量采用意译,因为舞台上人物不可能再给自己所用的典故加注说明。例如,莎士比亚的The Two Noble Kinsmen(《两个高贵的亲戚》)的第一幕第一场中Theseus(忒修斯)的一段话中有Not Juno's mantle fairer than your tresses之句,而其中的Juno其实就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主的Zeus的高傲的王后Hera的别称,这段话中还提到了Mars's altar以及Hercules.如果译者不作任何增益将这些名字一古脑儿抛给不熟悉希腊神话的中国观众,那观众一定会如坠五里雾中。较好的办法是将Juno译为"仙后",将Mars译为"战神",将Hercules译为"大力神"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当然,如果译文只是供人阅读的,那就可采用直译加注,如梁实秋先生译莎士比亚就是以直译为主,必要时加一些注解,"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其译文这也是剧本翻译的一种。影视脚本的翻译,主要是为影视配音。影视艺术的特点,决定了影视语言的大众性,翻译时应力避生涩艰深难懂之词,习语典故也应以意译为主。影视翻译与普通小说翻译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时间。屏幕上演员说话时间如只有五秒钟,那译文的字数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员已经闭嘴,而配音却仍在说话,这对于译者是一个考验。同时,译文还必须照顾到演员说话过程中的停顿。如Memories are wonderful…and the good ones…stick to you like glue. (回忆是美好的…好的回忆……将伴你终身。)如要将stick to you like glue译为"将象胶一样始终粘着你",那就太长了。配音要想逼真,还要考虑选词的口形与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来说,嘴巴张得较大,译时应选择开口呼的汉字,反之则选用闭口呼的汉字。此外,译者必须关注屏幕人物的动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语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乐、粗俗高雅。
如果说翻译难的话,那么最难莫过于译诗了,尤其是格律诗,所以古今中外常有"诗不可译"的声音。其实,说"诗不可译",主要是指诗味难译,诗的音韵美难译,并不是说诗歌不能翻译。再者,诗有不同的诗:有的明白畅晓,有的艰深晦涩,有的韵律严整,有的不受律法所限。译诗者也有水平高低之分、技艺优劣之别,所以更客观地讲,诗难译但并非不可译。
一般说来,语言形式服务于内容,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就诗歌而言,形式的意义远远大于散文类作品中的语言形式。诗之所以成为诗,怎样说与说了什么同样重要,所以译文中追求形似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我国的译诗史上,有将英语格律诗译成元曲形式的,有将它译成五言古体形式的,还有用骚体译出的。但目前看来,采用这些形式都值得商榷,因为英语诗人绝不会写出唐诗宋词。同样的原因,把英语格律诗译成散文或散文诗(如梁遇春译雪莱的A Lament)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诗歌的形式是有意义的。英文格律诗汉译的另一种方法是"以顿代步",即以汉语的"顿"代替英语的"音步"以再现原诗的节奏。"以顿代步法"通常强调原文的韵式也应在译文中加以复制,即如果原文的韵式是ABAB、CDCD,那么译文也应有同样的韵式。所谓"顿",是指两个、三个抑或是四个汉字放在一起,它们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同时又形成语音的一种自然的起落。这确实有点像由轻重抑扬构成的音步。以这种方法译诗,是译者追求形似并再现音美的大胆探索,而且确实也产生了一些形神皆似的译作。不过,在顿与音步的对等方面以及顿在何处(即在何处停顿)等问题上,翻译界仍有争议,译者自己有时也难以把握。英语格律诗的另一种译法就是放弃韵律,用自由体翻译,持此论者的理由是原诗节律在汉语中无对等物,译诗重在传达神韵,形似难求且束缚表达,因此不如弃之。在追求形似上,我们认为,王佐良先生提倡的"以诗译诗"是完全正确的,诗歌毕竟不是散文,因此,原诗如果有韵,那么译诗也应尽量沿用;原诗如果无韵,译诗也应无韵,即使用韵,也不能太过整齐,只应是个别诗句中用韵。原诗的节奏应尽量用汉语的自然起落体现,但不可偏执,非要找到所谓"顿"与"音步"的等量齐观不可。形似应尽量在用韵与否以及诗行长短上予以体现,这样既保存了原诗的形,又再现了原诗的音美。当然,诗之最大功用是言志言情。传达情志当为译者首先必须考虑的事情。对于大多数诗来说,形式虽也有意义,但相对于诗之神韵和意境而言,它仍处于次要地位。英汉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常要求译者"变换说法",即变换形式以求神似。比如我们虽不赞成将英语格律诗全都译为中国五言或七言诗,但以这种形式译出的某些诗如能做到传神,却也不失为好的译作。诗歌形式中确有一些不可译因素,但诗的意义、意境、神韵却大都可以被意会、被言传,尽管难以全部传达。因此译者应在词语的锤炼上下苦功夫,写诗者常常是"语不惊人誓不休",译诗者没有这种精神也休想"译语惊人".试比较下面一个英语诗节的汉译: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译文一:
牛羊相呼,迂回草径
农人荷锄归,蹒跚而行
把全盘世界剩给我与黄昏 (郭沫若译)
译文二:
晚钟响起来一阵阵给白昼报丧,
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声起落。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
把整个世界给了黄昏与我。(卞之琳译)
译文三:
晚钟殷殷响,夕阳已西沉,
群牛呼叫归,迂回走草径,
农人荷锄犁,倦倦回家门,
惟我立旷野,独自对黄昏。(丰华瞻译)
二、 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翻译
(一) 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语言特点
剧本与小说、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对话写成的。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小说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读(当然也可以朗读),而剧本却是最终要诉诸声形的(当然也可以拿来默读)。剧本中的对话(对白)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经过作家精炼后的诗句,如莎士比亚的诗剧中,人物语言多是诗的语言,正式程度较高,辞格也较多。第二种是经过作家加工后的较为正规的、完整的语言,它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再一种就是未经加工的生活语言照录,多停顿,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语法规范句,多重复。当然,上述三种只是大致分类,在每一种类型中,语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语特点又会因人物的年龄、性别、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话语单调乏味,有的人则出语机智幽默,有的人言语矫柔造作,有的人则语言朴实自然……总之,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语言。
(二) 剧本的翻译
翻译舞台剧剧本和影视脚本,要充分考虑其上述特点,译好人物语言,充分体现原剧整体语言特色和具体的每个人的语言特色,使语言连同人物一起"活"起来,"动"起来。就舞台剧剧本的翻译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该剧在另一个国度用另一种语言演出服务,二是译出来供人阅读。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译者都应考虑原文作为剧本的特点。如朱生豪在译莎士比亚剧本时,常常要让自己扮作剧中人物,拿译出的句子读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如果戏剧翻译是为上述第一种目的,译者应尽量使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传达原文剧中人物的意趣,遇到习语典故,应尽量采用意译,因为舞台上人物不可能再给自己所用的典故加注说明。例如,莎士比亚的The Two Noble Kinsmen(《两个高贵的亲戚》)的第一幕第一场中Theseus(忒修斯)的一段话中有Not Juno's mantle fairer than your tresses之句,而其中的Juno其实就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主的Zeus的高傲的王后Hera的别称,这段话中还提到了Mars's altar以及Hercules.如果译者不作任何增益将这些名字一古脑儿抛给不熟悉希腊神话的中国观众,那观众一定会如坠五里雾中。较好的办法是将Juno译为"仙后",将Mars译为"战神",将Hercules译为"大力神"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当然,如果译文只是供人阅读的,那就可采用直译加注,如梁实秋先生译莎士比亚就是以直译为主,必要时加一些注解,"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其译文这也是剧本翻译的一种。影视脚本的翻译,主要是为影视配音。影视艺术的特点,决定了影视语言的大众性,翻译时应力避生涩艰深难懂之词,习语典故也应以意译为主。影视翻译与普通小说翻译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时间。屏幕上演员说话时间如只有五秒钟,那译文的字数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员已经闭嘴,而配音却仍在说话,这对于译者是一个考验。同时,译文还必须照顾到演员说话过程中的停顿。如Memories are wonderful…and the good ones…stick to you like glue. (回忆是美好的…好的回忆……将伴你终身。)如要将stick to you like glue译为"将象胶一样始终粘着你",那就太长了。配音要想逼真,还要考虑选词的口形与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来说,嘴巴张得较大,译时应选择开口呼的汉字,反之则选用闭口呼的汉字。此外,译者必须关注屏幕人物的动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语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乐、粗俗高雅。

重点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