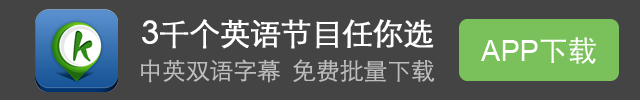(单词翻译:单击)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 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注意力会突然集中,并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语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语言之美,多体现在书面语上。讲话不能像背书;同样,写作也不能像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写到:“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师上来就是一个大红道:“Too chatty! This is not writing!”。当我连续使用同一个结构时,老师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个词在相邻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老师会划出该词,并批上“Bad style!”的字样。老师改过几次作文之后,我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入选的有吴一安、秦秀白、王英凡、唐闻生和我等9个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班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办这个班的初衷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高级外交翻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伊莎白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虽然没有当上大翻译,我的朗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一年长的出息。二是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Beijing Review(那时叫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学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译法,包括“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粮为纲”等。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小说原著的人刚接触Beijing Review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语不是为这种中国式的表达而造的。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尽管有人常批评China Daily和Beijing Review的英文有很浓的中文味,但是这种英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而且,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种变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总可以找到解释原文的方法。有点中国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乡土气息,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短语,只能先直译过去,再加个长长的脚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拿Beijing Review做课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做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但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只是时间的先后顺序记不太清了。一是我们学了翻译,特别是汉译英。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他们都很有水平,上课也非常有趣。这门课使我认识到,英文不学到家,翻译是谈不上的。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汉语文字看似已懂,实则不然。例如,汉语的小句,在英语中要降格为从句,才能真正体现原文中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并保证译文准确、可读。翻译远不是词与词、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是做不了翻译的。比如遇到“摇羽毛扇的人”(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若直译为“the person who waves a goose-feather fan”,那就是败笔,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如果加上“mastermind”,就清楚多了(见《汉英词典》第1183页,外研社)。但有时这个典故也用作贬义,指在幕后操纵或出坏点子的人,这时,可译为“a person who pulls the strings―the string-puller”。不过,上述例子仍属于翻译中浅层的、局部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要想翻译《红楼梦》,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
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五年级学了不少《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文章。那是在1965年,全国正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教学上开始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进入了课堂。客观地说,《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是我国几十位翻译家花了多年的时间,经过反复推敲而打造出来的一部精品。裘克安、庄绎传老师都参加过此书的翻译,并给我们讲过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现在,没有人再拿英译《毛泽东选集》当课本了,或者有人始终看不起这样的翻译。但是,我要说,我们从英译《毛泽东选集》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体验翻译过程,认识翻译技巧,感受文化异同。举几个有趣的例子吧。当时我们每天背颂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乍一看,这句话简直没办法译成英文。等我读了英译文才知道,原来自己根本就没读懂原文。“阶级斗争”一词,我一直把它当作名词词组来看待,所以无法翻译。而英译文为:“Classes struggle, some classes triumph, others are eliminated. Such is history, such is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译得妙极了。有些中国俗语译成英文也相当困难,要想译得准确、地道,必须要下一番工夫。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说,“凡事应该动脑筋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英译文为:“We should always use our brains and think everything over carefully. A common saying goes:‘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 In other words, much thinking yields wisdom. ”注意,第一句加了主语“We”,“hit upon a stratagem”译得好,还有“yield”也用得恰到好处。这些用词,只有英语语言造诣极深的人才想得出来。另一条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仅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英译文为:“In approaching a problem a Marxist should see the whole as well as the parts. A frog in a well says, ‘The sky is no bigger than the mouth of the well.’ That is untrue, for the sky i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mouth of the well.”注意,这里的“no bigger than”用得好,“the mouth”加得准确,将“坐”字漏掉,处理得好,“the size”又巧妙地避免了重复。
回忆起来,在北外学习期间,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那时,虽然我们没有“快译通”、“文曲星”等“现代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作业改得细致到家,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真庆幸,那时“托福”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时也觉得学了不少英文,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教过几年书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其说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首先,在备课时,我通过大量查词典,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备课时,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有些词是先查英英词典,再查英汉词典;有些是先查汉英词典,再查英英词典。查词典的过程中,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时在一个词上花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接着,我就借助词典,参考教案,转述(paraphrase)课文上的难句。一节课准备下来,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以便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的口、笔语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使”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二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5―6条新闻,写出7―8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刘承沛老师拿过笔来唰唰就改。不一会儿,我写的东西就变得面目全非。他下笔之快,用词之准,文体之潇洒,实在让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对我这份“兼职”的最好回报。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还有,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我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翻译、报刊阅读。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讲得深,学生才不至于浮在表面。为此,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社会意义、文体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老师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不仅有语言信息,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课上得引人入胜,师生双方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质量(教育家叶澜先生语)都得到提升。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和文化书籍等。有一次,为了讲几篇有关中东的报刊文章,我把中东战争史查了个遍。学生听得异常兴奋,无意中就吸收了很多信息和语言知识。为了把历史讲解得更生动、精彩,我随后还阅读了《邱吉尔战争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这批书从另一方面开阔了我的视野。这些书都是关于当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史料翔实,风格大气,语言堪称精品。特别是邱吉尔的书,气势宏伟,场面壮观,思想深刻,充满智慧。他的语言使我对语言的力量与神奇感到惊讶。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 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看到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我们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实的。两位先生让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研究生班开班不久,许国璋先生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参观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他站在离书架三米开外的地方说,“要练出两种本事。一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一部书,也就是说,要记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系资料室的某一个section应该有的书。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们缺某部词典(O.E.D.),或缺某种杂志(如美国的Language)。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书架 Language杂志合订本前,他得意地说,“我们是最近才开始订Language 的,我还亲自给杂志社写信,把过期的几十期统统补齐了。要等现在再补,可能已经绝版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他在多处驻足,评说着词典、百科全书、companion(指南)、文学名著、文艺批评、西方哲学、文化、历史等书籍及国内外的多种杂志。让我们吃惊的是,点评哪个角落的书,他都如数家珍。若某本书不在,他会发现放错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员询问书的去处。他还说,书要年年购买,要留意国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书就一定买到,否则别人会笑话。言谈之中,他对书的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参观在弟子们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对北外的图书馆熟悉到这个份上?
此外,我们那个研究生班还有幸请到多位外国专家来讲学。讲语言学的是英国人John Reed。此人闲话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接触普通语言学。我们这些毫无语言学根底的人,首次读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但还没有看到他的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记得那时我们对lange和parole,signifier 和signified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鲜。当时因为图书资料奇缺,我就把Reed 先生的7、8讲的讲课录音一字不漏地听写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听写,许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我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另一位讲语言学的是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安东尼先生,一位热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十年文革使我们对外界了解甚少)。尽管这些信息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新鲜。还有一位教英国文学的专家是英国文化处派来的布朗先生,此公学问不错,但是态度傲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愤怒的青年人运动”(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这里,我不是单纯列举事实,而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因为深感自己耳目闭塞,因此下定了奋起直追的决心。当时的十几名学生学习起来如饥人觅食,势不可挡。拿到一部经典、名著,常爱不释手,读个通宵。读研究生的前两年,我就写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评论“愤怒的青年人运动。”我读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阅了当时(60年代)的社会背景,又读了重要作家对此次文学运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先用英文成稿,交给布朗先生一阅。他大为高兴,在我的文章后批上“Tour de force” (法语,意为“出色之作”),他还当面对我说:“I fee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后,这个傲慢的人也变得友善了许多。得到鼓励后,我大着胆子把文章给王佐良先生看。几天之后,他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把文章译成中文,明年三月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第一期给你登一登。”还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乔姆斯基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于第二年发表在复旦主办的《现代英语研究》上。那似乎是国内生成音位学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是许老让我读了这本书。读过之后,我用英文写了个paper,并将文章给安东尼先生看。他说:“It’s very good. You’re a complex person. 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听了他的话,我放心了。接着,我又把文章变成汉语,给许老看。许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后面那些元音重读规则过于技术性,他没有看,就说,“你寄出去,让他们去改吧,复旦会有人懂。虽然那篇文章只介绍了乔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简单的三章,但它的发表给一个初学者带来的自信与愉悦却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读懂当代最深奥的音位学了。
总之,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藉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每个人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学问与教学的精细。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惟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象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试代替学习,不要用试题集代替课本。目前,应试教育现象十分普遍,考试过多,很多试题或题型不够科学。学习者花了很多的时间做题,最后拿个什么证,但是英文却没有学到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一门外语,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中有死记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学习词汇、语法等,是硬记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但是,使用语言,却需要多练,是艺术性的工作。现在的考试,多半是多项选择题,这种题型,易于测词汇、语法知识,不容易测出语言运用能力。再加上写作所占的比例太低,又没有口语考试,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很高,但语言运用能力却十分低下。目前,拥有各种外语证书的人已经达到几千万了,为什么外语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学习者:“凡是经过突击可以提高分数的考试,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试;凡是用大量的上课时间教你考试技巧的老师,决不是真正负责的老师;靠划ABCD是永远学不好英语的。我劝学习者不要太在乎拿个什么证,那不过是中国的‘土粮票’,是自我安慰。中国加入WTO后,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职者的英语能力,才不会去理睬你手中的那个证书呢。国际人才竞争,要靠本事吃饭;七大姑八大姨没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证书也不值钱了,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真正的英文吧。”
动笔之前,我决心要写出几句有意义的话来,以免愧对读者。但写完之后回头一看,不过是一本流水账。可见,一个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难啊。因此,以上文字,与其说是想给读者什么启迪与教诲,还不如说是在重温自己的学习经历,回忆自己在与恩师的交往中所获得的心灵的愉悦与精神的升华。
小编寄语:Daisy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崇拜刘润清老先生啦。虽然时代在变,但是有些人的知识和人品值得我们尊敬的。